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医生早已不再仅凭经验为病人做出诊断,证据才是医生最为核心的治疗依据,诊疗要遵循循证医学的理念。
循证医学是将最佳证据、医生的临床经验、病人的需求和价值观三者结合起来,对病人开展最有利的临床决策。其核心思想是在充分考虑病人意愿的条件下,医务人员严谨地、规范地、全面地运用在科学研究中得到的最新、最佳的证据来诊治病人。(详情点击:循证医学30年专题)
至今,循证医学在中国推广已有20多年,对我国医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医学生、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会根据科学研究得来的证据优化决策。在循证医学诞生30周年之际,健康界联合威科医疗UpToDate“循证医学30年·践行者系列访谈”专访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循证医学中心副主任陈世耀。他希望,未来所有医生都能将循证医学贯穿到每一天每一个病人的临床治疗当中。
循证医学让医学院校老师不再是“最正确的权威”
循证医学被带到中国,还有一段“漂洋过海”的经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进了临床流行病学,在原国家卫生部和世界银行资助下派出了一批临床医生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临床流行病学培训中心学习,中国也成为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INCLEN)成员单位。
回国后,各地专家自1986年起先后在各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临床流行病学课程,原上海医科大学和华西医学院批准成为我国的第二个临床流行病学地区与资源培训中心(R-CERTC)。在INCLEN支持下,以双语培养了大批临床流行病骨干。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全国的循证医学骨干。
1996年,王吉耀教授首次将Evidence-based medicine翻译为循证医学。2002年,王吉耀教授主编的《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的专著。
时至今日,循证医学早已成为医学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作为我国循证医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陈世耀多年来致力于在教学中培养更多具备循证医学思维的学生,在临床中为病人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多年来,陈世耀感觉到,中国医生对循证医学有了更好的认识,绝大多数医生在临床中会强调证据,结合病人的感受和价值观,进行自己的诊疗工作。与此同时,很多医生在处理疑难危重症病人时,建立了检索的意识,并努力去突破指南,从而让诊疗水平不断提升,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医生树立循证医学理念后所发生的变化。
陈世耀还记得,30年前自己刚刚步入医学殿堂的时候,所学科目中还没有循证医学这一课程,当时只有公共卫生中的一些方法学理念,并且与临床结合相对较弱。直到陈世耀成为一名住院医生时,才开始接受循证医学方面的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循证医学在不断发展,课程体系亦在不断变化。
“我以前做住院医生有不懂的地方时,会去问我的上级医生。现在的年轻医生遇到问题时,他可以问上级医生,但更多时候会借助于网络去查循证医学的资源,比如UpToDate,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年轻医生有更多的‘老师’,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他去探索疾病的治疗方式。”陈世耀相信,相比几十年前,在循证医学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医生更愿意去思考和研究,这是医学发展带来的改变。当然,这也给医学院校的老师们带来更大的挑战,他们不再是“绝对的权威”。
“在医学院校中,老中青三代教师都已经成长起来。相比过去,师资队伍更加强大,因为他们都经过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教育,这标志着医学生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到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专科培训,以及日常的医疗当中,都贯穿了循证医学理念。”陈世耀说。

检索工具持续为临床带来便利
当今的医学认为,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应以证据为基础或以证据为依据。而循证医学教育正是为了让医生依据证据提供最佳的临床解决方案。
循证医学讲究证据。证据包括基础研究证据、临床研究证据、群体研究证据。临床实践中,循证医学证据更加关注来自临床、以病人为研究对象的临床研究证据。陈世耀提到,临床中,医生使用任何证据前,必须对证据进行严格的评价。将证据用于解决病人问题时,必须将获得的证据与病人充分沟通后,了解并尊重病人的意愿,在病人理解和同意的基础上实施医疗行为。
临床实践应当考虑病人及其家庭、社会、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费用支付者的感受和能力。对于需要长期治疗或观察的疾病,不但要考虑近期的情况,还要考虑中长期的疾病治疗负担和预后情况。此时,医生应该提供足够的各方面证据信息,与病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共同做出适合病人的临床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循证医学提倡将临床医生个人的临床实践经验与最佳的临床证据结合起来,为病人的诊治做出最优决策,这是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陈世耀表示,忽视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即使是得到了最好的证据也可能用错,因为最好的临床证据在用于每一个具体病人时,必须因人而异,结合个体病人的临床特征与状态进行取舍。如果缺乏最好、最新的外部证据,临床医生可能应用已经过时的旧方法,这样就没能给病人带来最优决策,甚至造成损害。
当然,临床医生的实践经验也是一种循证医学证据。但是,单纯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据级别很低,而结合文献结果与临床实践经验往往比文献本身的证据级别更高。
陈世耀告诉健康界,证据可以通过文献检索获得,有一系列文献检索的策略可协助临床医师快速获取需要的证据。但是数量庞大,评价需要更多时间和能力。
简便的办法是直接寻找最新的临床实践指南。指南之后发表的系统综述,系统综述之后发表的原始研究,这一策略不仅省略了对指南与系统综述纳入大量文献的评价,更可以获得最新的临床研究结果。
陈世耀特别强调,利用循证医学工具评估特定的疾病或状态,实施个体化循证决策是当下的重要方向。比如,UpToDate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里面的作者就是专家,并且已经完善到拥有了中文版本。“UpToDate每一条意见都会标出原始文献作为证据,如果查询者对相关的意见或专家所推荐的治疗方法心存质疑,可以通过标注去查询原始文献。“陈世耀表示,这样的循证医学工具也推荐给本院的医生使用,特别是遇到疑难病例或者有争议的时候,可以参考国际上对于这类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这也是突破指南来实践应用的例子。
对于循证医学、精准医学、医学指南、新冠流行等问题,陈世耀亦给出了自己的研判。
健康界:你是否认为循证医学的理念如今已根植于国内所有医生的内心?
陈世耀:基层医生在这方面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无论是二级医院还是社区卫生中心,在接诊常见病的时候,大家都会参考指南。但在遇到疑难病例的时候,对循证医学的理念的贯彻就有所欠缺。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那里的医生所获得的学习和培训机会越少,诊疗过程中便越不会遵循指南,也由此消耗了更多卫生资源。
我曾经参加过援疆和援藏的项目,发现推广医疗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正确的疾病诊疗理念带给那里的医生,让他们理解“讲证据”的重要性,由此带来理念上的改变。
健康界:中国为何要制定更符合中国病人情况的诊疗指南?
陈世耀:临床指南的制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尽管循证指南促进临床诊疗进入了新时代,但指南本身并不能确保临床诊疗规范。如何让临床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使用高质量的证据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中国也必须有自己的指南,因为我们的病人跟西方国家的病人不完全一样。
另外,指南会成为“国策”,就需要跟上医保报销,要求对所有病人按照规范去做。因此在制定指南时,要考虑到中国病人和医保的承受和支付能力,也就是要符合国情。比如一名脏器衰竭的病人,国外的指南推荐病人进入移植的备选行列,但是我们的遗体和器官捐献理念尚未普及,也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接受这种治疗理念。因此,盲目跟着别人去推荐指南里的治疗方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另外,指南也在不断发展,一般四到五年就有新的指南出现。医生不能总想着突破指南,更多的时候是要按照指南去做,并学会根据病人情况去评价证据和指南。对于那些多次尝试治疗失败的病人,医生也要跳出指南,而不仅仅是告诉病人:“这个病没治了”。大家要开展新的研究,要去跟病人沟通,让病人加入到医生的研究当中。我们的指南不仅是为了服务医生,更多时候是服务于病人,因为医生最终的目的是为所有的病人服务。
健康界:你是如何看待“精准医学将取代循证医学”这种说法的?
陈世耀:精准医学最早在肿瘤研究中提出,针对肿瘤分子分型与特点开发靶向药物治疗。精准医学是循证医学个体化理念在肿瘤领域针对分子分型进行决策的具体应用,因为循证医学也强调个体化。在循证医学当中,每一个证据都要不断细化,不断去分层。比如说这个证据对成人有效,对儿童没有效;这个证据对成人当中的男性有效,对女性没有效;这个证据对成人男性中处于早期的疾病有效,对晚期就没有效。
当前,在肿瘤分子诊断与靶向药物开发、评价以及临床应用中,同样需要遵循循证医学理念。一是针对肿瘤病人的处理仍然需要强调一般生物学特征与社会经济学特征;二是强调肿瘤病人的分子靶标同样需要循证医学证据,尤其是大样本、多中心、针对不同肿瘤、不同肿瘤病人状态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每一个肿瘤分子标志物,都可以理解为疾病的一种临床病理状态。
健康界:你认为,新冠大流行会给循证医学带来哪些挑战?
陈世耀:所有新发疾病都在迫使医生去认识这个疾病,并找到治疗方法。我们通过不断接触新病例,积累更多样本,为循证医学提供更多的证据。公共卫生还会涉及到疾病在人群中传播的变化过程。我们看到,新冠的毒力虽然越来越弱,但传染性越来越强,这些变化也会纳入到循证医学证据当中,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循证决策。
新发传染病处理的决策除了临床数据,还涉及人群数据来源的证据、社会学、经济学、价值观,和政策考量等多方因素,这些都是新冠流行给循证医学带来的挑战。
健康界:对于循证医学的未来,你有哪些展望?。
陈世耀:首先,未来所有医生都能将循证医学贯穿到每一天每一个病人的临床治疗当中。第二,证据会越来越丰富。
第三,循证医学的证据收集和评价会变得更方便。机器人不仅可以做这些事情,还能在诊疗过程中做计算和文献查找。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都会更加有助于循证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提供证据评价和决策方面,将给予医生更多的支持。

来源:健康界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考研学习网 »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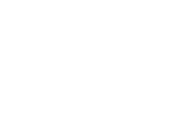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部)
